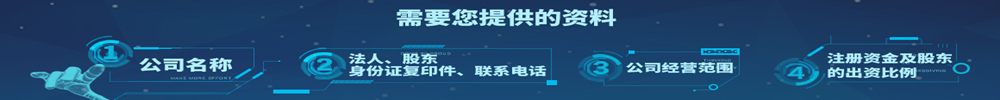一座“吃人的桥”:环卫工频被撞荧光服等形同虚设
环卫工之殇:倒在“吃人的桥”
在哈尔滨二环桥上,飞驰的轿车两次撞倒了这个环卫工家庭。
事发都是凌晨,环卫服反射出清冷的荧光,与暖黄色路灯和车灯辉映,守护着城市黎明前的梦境。张洪文和老伴孙贵芳的扫帚划过路面,沙沙声起伏。
突如其来的撞击声,刺破夜空,紧接着是哭喊声、警笛声。张洪文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场景,是5年前。一辆面包车从他背后飞快驶来,他只记得自己砰然倒地。
这一次,倒下的是孙贵芳。她再也没有醒来。
12月22日,孙贵芳和4名同事在清雪作业时被一辆轿车撞倒,事故中有4人当场死亡,1人经抢救无效身亡。
新闻很快就会成为旧闻。正如哈尔滨今年发生的另几起交通事故:新年第一天,两名环卫工在二环桥上被撞身亡,拖拽几十米;上个月中旬,初雪降临后数日,两名环卫工在道里区清雪时被撞死;12月10日,哈尔滨遭遇今冬最大降雪,公路大桥上3名环卫工被撞,一死两伤。
肇事司机醉酒驾驶
张洪文接到电话,是22日凌晨5时许。他冲到二环桥康安路段上,一辆黑色尼桑轿车撞烂了车头,挡风玻璃破碎。几名穿着工作服的环卫工,一动不动地躺在事故车道对侧,路面散落着被撞碎的扫帚条。59岁的孙贵芳就在其中。
22日6时许,马明华赶到桥上时,死亡的老伴齐连义已被送走。为了寻找爱人,这名左脚没有脚趾的女人,先一瘸一拐赶到医院,扑了个空,她又穿过康安路大发市场,逆行走上车流不息的二环桥。
事故大约发生在4时40分,当时11名环卫工正在清扫桥面,肇事车辆从后方驶来,绕过打着双闪的环卫车,冲向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。4人当场死亡,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,两人受伤。经警方初步调查,现场没有看到刹车痕迹,肇事司机为醉酒驾驶,血液乙醇检测值为146.19mg/100ml。
“这就是故意杀人。”张洪文喃喃地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老伴走后第3天,他依然吃不下东西。
他不是第一次见识“吃人的桥”。2012年9月的一天,大约5时,他在二环桥一个下引桥处作业,突然被撞得不省人事。
他昏迷了半个月,腿也被撞折了,动了两次手术。因为一年多没上班,肇事司机垫了医药费,赔了3万元误工费。伤养好后,张洪文继续做环卫工,“找不到别的活计”。只不过,从此换到桥下。
老伴儿孙贵芳仍在桥上干活。因为扫地干净,她成了小组组长,手下管着四五名工人,并且每月能多领100元“操心费”。
环卫工又被撞死的消息,很快在哈尔滨道里区新学街传开。因为房租便宜,居住在此的大多是环卫工、清洁工和杵大岗的(靠卖苦力打杂的人——记者注)。
同在这场车祸中丧生的齐连义,也住在新学街。他今年55岁,来自佳木斯,街坊邻居都叫他“齐老三”。离婚后,经人介绍,他认识了来自辽宁本溪的马明华,俩人没登记,但感情很好,出门常手挽着手。
据马明华回忆,一贯沉默寡言的齐连义曾提过一次,“桥上太危险,不想干了。”他们商量,再凑合着对付几个月,然后回农村种地,或者给人开插秧车。
“谁有高招”
张洪文的侄女和侄女婿,也是环卫工,住得很近。出事后,他们请了两天假,第三天早上,俩人又和平常一样扫街去了。
侄女说, “这工作就是和车赛跑”。她在桥下工作,每天盯着车辆,车少时,她赶紧冲到马路上,把过路车辆和路人丢弃的垃圾扒到一边。它们可能是任何东西:烟头、纸屑、易拉罐、饮料瓶、呕吐物,有时甚至是粪便。
有些“素质高点”的车主,瞅到她会主动停车,摇下窗,将垃圾扔进她的塑料兜里。不过,“素质高的还是少”。
桥上的工作更危险,车撞过来的时候,躲都没地方躲。每天清晨,除非起雾或下雨,环卫工都要对桥面进行清扫。
在新学街,人们并非不知晓这份工作的危险性。车祸次日,交接班的间隙里,身穿环卫服的人们短暂地停留在食杂店门口,神色凝重。
频发的事故,让环卫工人人自危。安全措施在一步步升级,从荧光服、反光条到爆闪灯、反光锥,警示标志越来越多。然而,在不守规矩的车辆面前,它们形同虚设。
一名环卫工告诉记者,单位领导也很重视安全问题,但也苦于找不到解决办法。领导甚至召集大家开会问:“谁有高招?”
新学街的环卫工几乎都是外地人、临时工,年纪在五六十岁上下,没社保。“干这份工作,脑袋系在裤腰带上”,谁都心知肚明,但谁也离不开。好歹,一个月能挣2000元,比扫楼挣得多。在桥上工作,每月还能再多100元,逢年过节单位给发大米和面条。
张洪文和孙贵芳从庆安县来到这里,是为了还债。给儿子娶媳妇时,他们卖了老家的房地,还欠下十七八万元。
老两口在新学街租了一间每月120元租金的棚屋。十多年过去,债务总算只剩几万元。日子开始有了盼头,张洪文在小桌摆上自家酿的酒,他平时好这口。
下班后,他有时上附近的茶馆坐坐,里面大多是环卫工或清洁工,扑克一角一局,麻将二角。对他们来说,这几乎是唯一的消遣。
齐连义不爱上茶馆。他和马明华没事就在家中。
环卫工每天可以凭卡领5元买早餐,但齐连义几乎从来不领。他总是攒上一个月,换些更实用的东西。他家门外有台二手洗衣机,找别人借的,在这片没有自来水和暖气的棚区里,算是个稀罕家当。马明华常招呼邻居付连凤,“付姐,衣服拿来洗!”
64岁的付连凤在一家店里做清洁工。她也曾做过环卫工,当过组长,“实在扛不住冻了”才换工作。那几年,她琢磨出很多干活的窍门,“冬天在袜子外套上塑料袋,站在风中脚就不会那么冷了”“把编织袋拆成一条一条的塑料带子,捆在一起做成扫把,清扫尘土特别管用”“她还在自己的扫把上缠了几根大红丝带”。
“前一天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”
出事后,张洪文把自己关在家里。亲人们从老家赶来,挤在六七平方米的出租屋里。屋子太小,挪不开脚,几个老爷们脱了鞋蜷在床上,另外几人抱着手臂靠在灶台边。
光线从糊着纸的天窗上漏下来,大伙儿故作轻松地磕着瓜子,张洪文发着呆,拿剃须刀一遍一遍地刮下巴上的胡渣。他告诉记者,脑袋里面都是那些事,和老伴的点点滴滴,“前一天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”。
孙贵芳和他同岁,大高个,爱说爱笑。他俩在一起20多年,却没有一张合影。
屋里已找不到老伴的痕迹。在哈尔滨另一个区收废品的儿子赶了过来,他抱出母亲的衣物,在巷口一把火烧掉。首先湮灭在火焰中的,就是母亲那套环卫工作服,衣服从鲜艳的荧绿色,化成黑色的灰烬。
亲属去了殡仪馆,张洪文想去,大家拦住他。挑寿衣时,有800元一套的,有1300元一套的,儿子打电话问买哪种。张洪文说,“买最贵的”。
张洪文说,干环卫工的十多年里,老伴儿每天都穿工作服。冬天,更是裹得严严实实,戴着雷锋帽,站在寒风中,只露出一双眼。
马明华终于在殡仪馆见到了齐连义的遗体。马明华嚎啕大哭起来,她用沙哑的声音吐出一句话,“想给齐老三买个墓,让他有个安稳的家”。
出事后的第三天,马明华抱出了老伴儿的衣物。在被积雪覆盖的垃圾堆里,那套有荧光条的环卫服格外扎眼。
最终,衣服堆到了邻居付连凤的出租屋中。她曾在医院干过保洁,不忌讳死人的东西。“人死了就没了,怕个啥?这些衣服多好啊,又干净,等开春了,新一批打工的人来了可以送给他们穿。”